
搜索专业人员
推荐专业人员:
2023-12-21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主观明知与情节严重的认定困境 ——基于台州市张某英等案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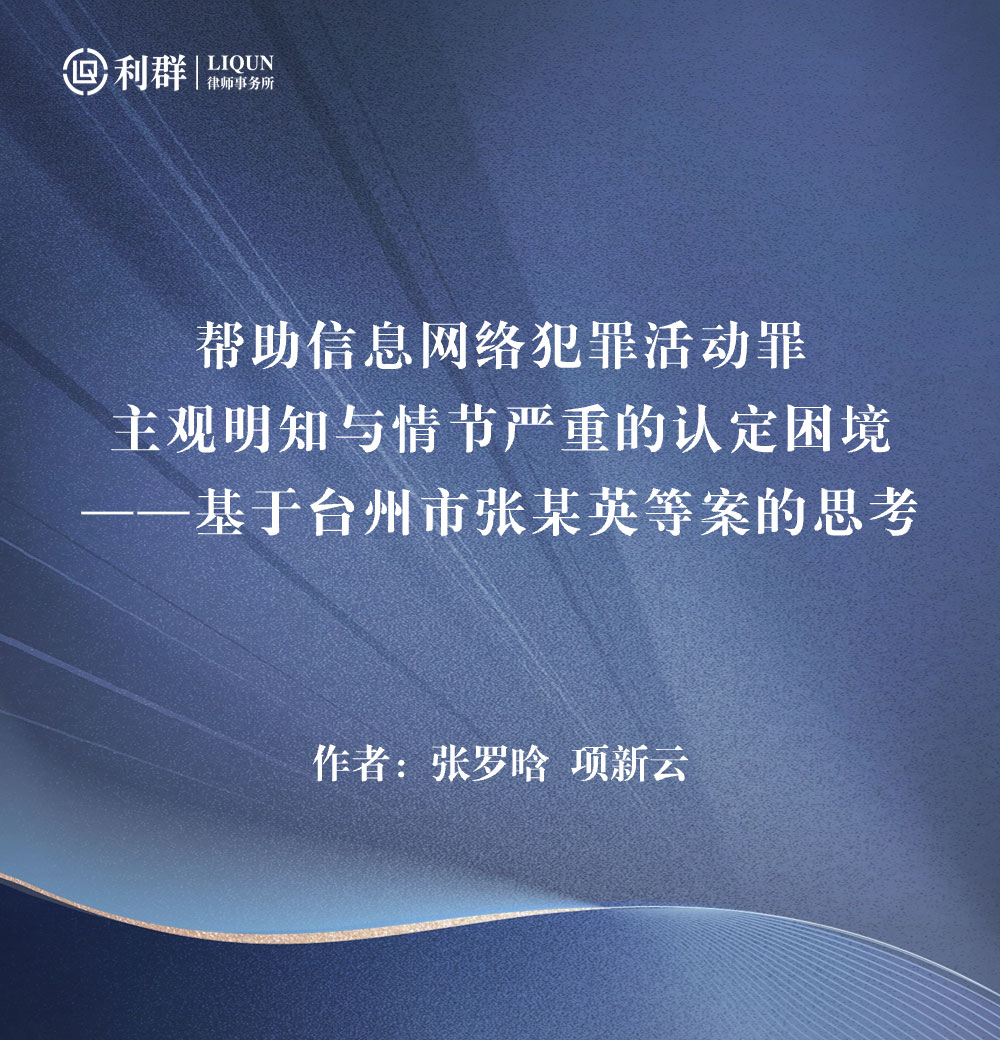
摘 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设立之初衷,系为规制近年来愈发泛滥的信息网络犯罪行为。但该罪近年来在《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加持之下,呈现出扩张适用的趋势,以该罪定罪论处的案件连年激增,甚至有沦为“口袋罪”的趋向。而台州市张某英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正是帮信罪司法适用扩张背景下的产物。本文以台州市张某英案为视角,并检索分析类案发现,当前司法实践中帮信罪主要出现“明知”认定畸形泛化、“情节严重”认定标准不一、裁判文书缺乏论证说理等问题。对此本文也基于对台州市张某英等案的论证分析,提出了严格限制“明知”的推定标准、明确“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强化裁判文书论证说理意识等破局之道。 关键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明知;情节严重
一、引 言
最高检于2021年4月23日发布2021年1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¹显示,统计排在前五位的起诉罪名分别是:危险驾驶罪(74713人);盗窃罪(45662人);诈骗罪(24173人);故意伤害罪(18749人);开设赌场罪(17897人)。最高检公布2021年三个季度的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显示²,仅半年时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79307个被起诉人次,同比上升21.3倍的绝对优势超过开设赌场罪,跃升成为排名第四的起诉罪名。至2022年第一季度,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最更是以33354人次远超诈骗类犯罪(4965人)和赌博类犯罪(3651人)³位居第三。而2023年仅第一季度,全国检察机关便已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2.5万人次⁴。 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的刑法罪名,但在2015年至2019年,该罪名并没有引发过多关注。直到2019年11月,《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的施行,以及“断卡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帮信罪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呈现出井喷的态势。与此同时,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客观要件司法认定标准不当泛化和司法工作人员重视“入罪”思维、忽视“出罪”思维的影响下,致使该罪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口袋化”的倾向,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司法机关消极侦查、消极指控,进而产生帮信罪“犯罪圈”不合理扩大、法律适用混乱等现象。
二、台州市张某英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一) 案情简介及审判结果 2019年10月,本案被告人张某英经其姐夫介绍了解到,在台州当地可以通过办理注册公司的方式获得高额无息贷款,即注册公司后可获得50万元贷款,并且30年内无需归还利息,30年期限届满若无偿债能力亦无需归还本金。被告人张某英受此高额无息贷款的利益诱惑,在绰号“小胖”的不法分子安排和带领下来到台州,注册了台州东铭远广告有限公司、台州市佬簿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台州市泽海广告有限公司、台州椒江稿枫五金店四家公司,并在银行开立相应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尔后,上述四家公司的公章、私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等悉数由“小胖”保管,四家公司的对公账户皆为“小胖”用于网络赌场的非法资金流转,资金流入高达6300余万元人民币,其中,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赵某参与网络赌博活动,充值赌资 40 余万元,转入台州市东铭远广告有限公司账户赌资金额 4 万余元。张某英从中未获益,“小胖”承诺的高额无息贷款也从未发放给张某英。 鉴于此,检察院对张某英提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一审法院认为张某英系初犯,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而最终判决时,一审人民法院未采纳检察院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转而判决张某英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⁵的实刑。虽然判决书中有简要列举公司登记基本情况,银行开户信息、交易明细等据以认定张某英罪行的证据,但对于张某英主观明知情况等缺少必要的论证。 (二)本案争议焦点 1.主观构成要件“明知”的认定 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行为人构成本罪需明知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本案控辩双方对于公司登记基本情况,银行开户信息、交易明细等证据无异议,但对于张某英的供述存在争议。因张某英在8份讯问笔录中,对于其主观认知情况的表述均为“担心过他们会拿我的公司账户去做违法的事情”,如此明知“可能违法”的供述,是否能作为认定张某英明知“小胖”等人信息网络犯罪的证据,仍存在一定的讨论空间。 2.“情节严重”的量刑标准 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行为人构成本罪需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分析本案的判决书不难发现,法院虽对张某英四家公司账户非法流水的金额、被帮助犯罪中一被害人赵某的损失进行列举,但缺乏认定张某英的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说理分许过程。被帮助犯罪的涉案金额以及社会危害性,是否能作为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行为人“情节严重”的量刑依据,是本案存在争议的焦点。
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的认定 (一)司法实践中对该罪“明知”的认定情况与偏差 1.缺乏对主观构成要件“明知”的具体论证 在北大法宝检索分析现有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公开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司法机关对于本罪“明知”的主观要件在具体案件中进行认定时,普遍存在缺乏说理的问题,这会导致行为人“明知”的认定陷入状况不明的境地。一方面体现在各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认定理由单一,大部分都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方式一笔带过,并未进行详细论证。例如温州市洞头区王某、李某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⁶的判决书“公诉机关认为”部分显示,检察机关在说理部分仅对王某、李某刚二人账户中非法流水的金额与被害人所受损失金额进行列举,忽视了对王某、李某刚二人主观“明知”情况的论证。又如嘉兴市南湖区孔某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⁷的判决书中显示,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只有简单的“被告人孔某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3张银行卡流转资金,支付结算金额达150万余元,属情节严重,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一句话表述,亦无对孔某昆主观“明知”情况的论证。可见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对该罪的整体认定上,更倾向于认为行为人客观上只要满足为犯罪提供帮助和情节严重的要件即可构罪,而不对“明知”的主观构成要件进行论证。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检察机关和法院缺少对行为人认识内容的审查。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角度出发,该罪要求行为人明知自身的行为系帮助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即对被帮助人犯罪行为的明知。因此,在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行为人的“明知”情况时,应着重分析行为人对被帮助者的行为认知情况。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多认为无论关联犯罪裁判与否,一旦能证明关联犯罪存在,就能对帮助行为定罪。这样的实践观点,一定程度上导致在大部分的判决在并未较多说明关联犯罪情节的情况下,便径直以行为人的获利、账户的非法流水等证据将犯罪的帮助行为认定为本罪。 2.“明知”内容的不当泛化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立的前提之一,而对于该构成要件中“犯罪”一词含义的界定在学界尚存争议,并由此衍生出狭义说、例外说和扩张说的三种观点⁸。其中,狭义说的观点认为,应当将“犯罪”解释为符合所有犯罪成立所需构成要件的行为。但此种观点较为狭隘,将导致帮信罪的关联犯罪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帮助者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再大也难以得到定罪处罚。这会使该罪立法目的落空,无法满足现实的打击帮助网络犯罪行为的需要。而例外说的观点认为,帮信罪中被帮助者的行为能构成犯罪即可,但在帮助人数较多、被帮助对象行为经查确属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行为但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证实、帮助者情节远超“情节严重”程度的三种情形下,即使被帮助者的行为尚未被定罪处罚,帮助者的行为也仍可被认定为帮信罪。扩张说则认为,为加大打击信息网络犯罪的力度,可以将帮信罪中的犯罪扩张解释为包含“违法”和“犯罪”,即帮助者主观上明知被帮助行为“可能违法”就能被认定为帮信罪。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也多采纳扩张说的观点,运用此种学说虽能有效打击帮信罪,但过于放宽标准可能间接导致帮信罪之处罚范围变相扩大,最终沦为“口袋罪”。 3.“明知”程度的过度扩张 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程度的认识,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明知”仅包含确切知道,即行为人主观上应当具有内心确信的认知状态;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明知”在确切知道的基础上可以扩张到应当知道,即行为人主观上并未形成确信,但在特定的情形下有极大概率能够预见行为人主观上应当知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明知”在包含明确知道外,还应包含推定知道,即在满足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尽管行为人主观上表现为不知,但根据其一定行为仍然可推定其明知。《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实际采纳了上述第二种观点,即对帮信罪中行为人主观认定采取“明知+应知”的模式。而参照《刑法》第十四条的表述,行为人需要对自身的行为性质有一定判断,并且希望或放任自身行为造成一定法律后果,才能构成“明知”。可见,《刑法》总则对“明知”程度的认定更偏向于“确切知道”,《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实质上在《刑法》总则规定的“明知”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扩张。 而司法机关近年来则在《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助力之下,多采用法律推定的方式来对帮信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认定。例如湖南省李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⁹的判决书中,检察机关以证明行为人知晓银行卡不得出借、出售或转租的方式径直推定王某主观上对被帮助的信息网络犯罪明知,进而认定其成立帮信罪。司法机关采取这种宽松的主观要素认定标准,虽在打击犯罪方面能取得一定成效,但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部分司法人员存在过于重视入罪,丧失帮信罪司法适用合理性的现象。 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程度的认识,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明知”仅包含确切知道,即行为人主观上应当具有内心确信的认知状态;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明知”在确切知道的基础上可以扩张到应当知道,即行为人主观上并未形成确信,但在特定的情形下有极大概率能够预见行为人主观上应当知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明知”在包含明确知道外,还应包含推定知道,即在满足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尽管行为人主观上表现为不知,但根据其一定行为仍然可推定其明知。《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实际采纳了上述第二种观点,即对帮信罪中行为人主观认定采取“明知+应知”的模式。而参照《刑法》第十四条的表述,行为人需要对自身的行为性质有一定判断,并且希望或放任自身行为造成一定法律后果,才能构成“明知”。可见,《刑法》总则对“明知”程度的认定更偏向于“确切知道”,《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实质上在《刑法》总则规定的“明知”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扩张。 而司法机关近年来则在《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助力之下,多采用法律推定的方式来对帮信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认定。例如湖南省李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的判决书中,检察机关以证明行为人知晓银行卡不得出借、出售或转租的方式径直推定王某主观上对被帮助的信息网络犯罪明知,进而认定其成立帮信罪。司法机关采取这种宽松的主观要素认定标准,虽在打击犯罪方面能取得一定成效,但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部分司法人员存在过于重视入罪,丧失帮信罪司法适用合理性的现象。 (二)本案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分析 本案中张某英的辩护人主张,张某英主观上始终认为“小胖”带领其开公司系为申请贷款,而非实施犯罪行为。张某英虽有“担心过他们会拿我的公司账户去做违法的事情”的表述,但不足以据此而认定张某英主观上确实明知“小胖”等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的情形,因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可能违法并不意味着能直接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犯罪。可见,检察机关在对本案进行认定时,以明知“违法”代替明知“犯罪”作为认定张某英主观明知的结论,这无疑忽视了甄别张某英主观上是否存在仅认识到一般违法的情形,变相扩张了帮信罪中“明知”所指向的内容,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明知”认定的偏差。 同时,张某英注册的四家公司以及相应的银行账户始终处于“小胖”的管理支配中,张某英并未有过任何操作。张某英对四家公司账户的资金流转不知情也无法知情。检察机关和法院仅以公司登记基本情况,银行开户信息、交易明细等证据来证明张某英主观“明知”的情况,论证依旧不充分,因为在证明张某英“可能知道”的同时,也意味着其“可能不知道”,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加以佐证并进行说理。
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一)司法实践中对该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情况与偏差 1.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认定现状 就当前的司法实务而言,司法机关对于帮信罪案件中“情节严重”的判定,多是基于司法解释中对“情节严重”情形的列举。在具体的司法适用中,司法机关认定帮信罪行为人“情节严重”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几种路径: (1)按照被害人人身损害后果认定。例如温州市鹿城区游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¹⁰中,他人使用游某提供的账户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行为,被害人谢某因不堪忍受巨额财产损失而跳楼身亡。法院认为被害人谢某的死亡与游某为关联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行为之间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以此将被害人死亡的人身损害后果归责于游某,进而认定游某满足帮信罪的“情节严重”要件。 (2)按照被害人遭受的损失认定。例如海宁市李某杰、李某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¹¹,法院审理查明关联犯罪中被帮助者利用李某杰、李某珺二人提供的账户诈骗四名被告人共计191万元资金,认为李某杰、李某珺二人的提供支付结算的行为结果已构成帮信罪“情节严重”的要件。法院如此的认定方式实际为间接因果关系的归责方式。 (3)按照涉案非法资金流水认定。例如温州市平阳县黄某剑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¹²,法院以黄某剑自己提供和伙同他人收 买的9张银行卡中2.6亿元的非法资金流水认定黄某剑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4)按照行为人非法获利数额、关联犯罪涉案金额、被害人损失等综合认定。例如袁某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¹³中,法院查明袁某清非法获利人民币10700元,被帮助者利用其账户支付结算金额共计人民币729800元的诈骗款,其中造成被害人繆某共计729800元的损失,法院以此认定袁某清满足帮信罪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 2.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认定偏差 基于信息网络犯罪的方式和方法、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类别和模式的日新月异的现状,以及规避立法出现滞后性和适应打击网络犯罪现实需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于“情节严重”这一构罪标准采用了概括性的立法技术。如此虽为帮信罪案件中“情节严重”的认定留出了一定弹性的解释空间,但也导致该罪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出现“情节严重”认定标准不清的问题。《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称《意见二》)和《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出台后,司法机关对帮信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变得有法可依,可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产生差异化理解、法官处理案件时的自由裁量之下,帮信罪“情节严重”的认定仍存在一定的适用偏差。 当前司法机关认定帮信罪中行为人“情节严重”的落脚点往往在于被帮助犯罪的行为结果,频繁使用间接因果关系的归责方式让帮信罪的行为人为被帮助犯罪的行为结果买单。如前文列举的温州市平阳县黄某剑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法院以黄某剑信用卡中因被帮助犯罪行为产生的2.6亿元人民币非法流水来认定黄某剑情节严重。司法机关如此的认定方式,实际上将帮信罪“情节严重”的标准与关联犯罪的具体情节混为一谈,直接将关联犯罪中的犯罪数额移植为帮信罪行为人的犯罪数额实属不妥。这样的认定方式,将帮信罪行为人和被帮助者实施关联犯罪的罪量混同,一方面不符“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刑法归责原则,另一方面也会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帮信罪行为人量刑的畸重,最终会使得帮信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走偏,导致司法适用的混乱。 当前司法机关认定帮信罪中行为人“情节严重”的同时也忽视了论证说理的工作。例如甘肃省马某拉、马某夫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¹⁴的判决书中,法院仅简单说明其二人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客观行为,在未论证其二人行为是否符合“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将马某拉、马某夫二人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如此判决难免缺失一定的严谨性。 (二)本案对“情节严重”的认定 本案张某英并未从其开立账户等行为中获利,司法机关系凭借“小胖”利用张某英四家公司账户结算的6300万元非法流水,以及被害人赵某因“小胖”开设网络赌场遭受40万元损失的情节认定张某英“情节严重”,系属前文所述的利用关联犯罪涉案金额、被害人损失等证据综合认定“情节严重”的。因此,张某英的辩护人主张,张某英系因法律意识的淡薄而被动犯罪,一开始只以为可以申请贷款,以为小胖让给他们弄的是贷款的流程,并非主动实施本案的犯罪行为,相较于其他典型的帮助网络信息活动罪的行为人,张某英的主观恶性较弱。 同时,张某英系为获得无息贷款而实施本案行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任何贷款,客观上也没有任何报酬获利。账户中6300万非法资金的流转实际上应归结为“小胖”等人开设赌场的违法行为,并不能以此数据作为对张某英量刑的依据,若让帮信罪中被告人过多为被帮助犯罪买单,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罪责刑之间的失衡,是对帮信罪行为人的过度苛责。
五、张某英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启示与思考 (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明知”认定完善路径 1.限缩解释帮信罪中行为人“明知”的内容 帮信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行为人主观上需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行为人“明知”所指向的“犯罪”,究竟要求达到违法的程度还是犯罪的程度,对该程度应作何种程度的理解是司法适用中的一大难题。而对“犯罪”含义的理解也会基于个人的立场或看待个案的不同视角而出现不同的解读。本文从限缩适用的视角看来,帮信罪行为人主观认知中的“犯罪”在程度上应以相应犯罪的入罪条件作为前提,并要求被帮助者确实利用帮信罪行为人提供的帮助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意即“犯罪”应当限缩解释为排斥一般违法行为的犯罪行为。首先,依照《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规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犯罪既包含犯罪行为,也包含程度尚未构成犯罪但属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行为类型的违法行为;其次,《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二款的罪名规定中仅要求被帮助人实施犯罪,而没有规定被帮助人实施违法行为。可见,对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两罪名中“违法犯罪”两词的界定在立法上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对于帮信罪中行为人“明知”内容所指向的“犯罪”,应当排除一般违法行为¹⁵。如此限缩解释帮信罪行为人“明知”的内容,有助于避免司法机关基于“入罪”的思维惯性而扩张帮信罪的适用范围,也有助于严格司法机关的办案过程,敦促司法机关加强对帮信罪行为人主观认知的审查和对“明知”的说理论证。 2.严格限定“明知”的推定标准 刑法具有广泛的引导公众行为的规范作用,在对帮信罪中行为人“明知”时应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为基础,因为现实中无法要求社会大众都具有接近于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意识和认知能力。因此,司法机关在对行为人主观认知进行认识是,应当结合行为人的文化水平、职业背景等多种元素来综合认定。一方面,行为人的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其对自身行为性质的辨识能力;另一方面对行为人职业背景的调查能够在主观“明知”要件认定过程中起到强化证明的作用。例如有网络技术从业背景的行为人认识到被帮助对象实施信息网络犯罪的概率相对一般人而言更大。 前文已阐述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将帮信罪中行为人主观“明知”程度扩张至应当知道,已经影响具体司法适用中帮信罪主观要件认定的合理性。在本文看来,帮信罪“明知”程度的标准应限缩至“确切知道”层面为宜。尽管“确切知道”的标准偏高,但基于一般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考量之下,将“确切知道”作为“明知”的解释更具司法适用的合理性,否则坚持扩张明知的推定标准至“应当知道”,会留给裁判者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难以把控具体幅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合理性,甚至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客观“情节严重”认定完善路径 1.明确与被帮助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衔接标准 前文已经分析过司法机关在“情节严重”认定过程中过分依赖关联犯罪的社会危害结果作为认定依据的情形。司法机关适用如此认定途径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对被帮助行为人客观行为认定与被帮助对象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之间论证衔接不明晰的情状。比如将关联犯罪导致被害人自杀的结果、被害人财产损失的结果、关联犯罪直接产生的巨额非法流水的严重后果直接作为帮信罪中认定行为人“情节严重”的依据,以弥补当前立法对于帮信罪尚无“情节严重”明确且统一认定标准的缺憾的做法,实际有失偏颇。因此当前亟需树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帮信罪与关联犯罪间的衔接标准,合理界定帮信罪行为人在关联犯罪中起到的作用,合理按照帮信罪行为人在对关联犯罪中影响力的大小分摊应有的刑事责任,而非一味的将关联犯罪的社会危害结果全部归结于行为人的帮助行为。 2.严格兜底性条款的适用条件 《信息网络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从被帮助者犯罪行为结果的危害性程度、帮助者行为恶性程度等方面出发,对帮信罪中“情节严重”情形进行了详细列举的同时,《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也以规定“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的形式作出兜底。然而,“情节严重”情形的分类列举并不意味着帮信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已然树立,如此兜底条款概括性的特征也会导致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不当扩大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实务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难以统一,增加司法机关“专断”的可能性。因此为避免帮信罪具体司法适用的不合理扩张,司法记挂在使用“情节严重”兜底条款的过程中应秉持谨慎态度,结合各项证据充分论证,以保证个案中出现的具体情形能够同等的具备乃至超出与当前法律列举的“情节严重”情形的社会危害性。此外,可以在后续法律的修订和司法解释制定中,针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进行说明或者补充。比如在帮信罪行为人违法所得计算规则方面加强标准的制定、限制被帮助犯罪流水金额在认定帮信罪行为人“情节严重”过程中的权重,以此来减少司法机关适用间接因果关系归责的方式,变相扩大帮信罪行为人为关联犯罪“买单”的范围。 (三)增强对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的重视程度 裁判文书作为权威的法律文书,在得出最终的罪与非罪的结论之前,应当有详实完整的事实认定以及法律推理的论证过程。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常出于“重视入罪”的惯性思维,认为行为人客观上符合为犯罪提供帮助和情节严重的要件即可构成帮信罪,而忽视对行为人主观认知的审查,忽视对“情节严重”的具体论证。裁判文书中说理论证的不充分,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对被告人定罪依据的支撑性不足,大大削弱文书的说服力。因此,帮信罪中行为人主观的“明知”和客观的“情节严重”作为认定罪与非罪的重要元素,司法实践中应当切实加强重视,严格贯彻落实对行为人“明知”和“情节严重”的认定以及说理标准,避免在缺乏论证的情状下,片面得出帮信罪中行为人有罪的结论。
六、结 语
诚然,信息网络犯罪的方式方法、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模式的日新月异增大了司法机关打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更好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就可以不加限制地扩张帮信罪司法适用的范围。在如今帮信罪有沦为“口袋罪”可能的现状之下,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在具体的案件中扭转重视“入罪”而忽视“出罪”的思维惯性,严格把控帮信罪主观“明知”构成要件和客观“情节严重”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在个案中明晰帮信罪与其关联犯罪之间的界限并审慎适用“间接因果关系”的归责方法,加强“罪与非罪”的说理论证才能够有效缓和帮信罪“犯罪圈”不合理扩大、法律适用混乱的矛盾现状,进而实现对帮信罪行为人定罪的准确与量刑的均衡。
参考文献
¹ 陈俊秀,岳美莲.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之扩张趋势及其限缩[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01):30-36.
² 莫洪宪,吕行.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与规范适用[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123-138.
³ 柳洁,卢军,龙钊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用问题探讨——基于100份有效判决书的分析[J].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2,37(06):119-128.
⁴ 毛斌.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认定困境及反思[J]. 证据科学,2022,30(06):730-742.
⁵ 侯婷婷.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限缩适用路径研究[J]. 西部学刊,2022,(18):61-64.
⁶ 张金灿.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问题研究[D].河南大学,2022.
⁷ 周振杰,赵春阳.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证研究——以1081份判决书为样本[J]. 法律适用,2022,(06):83-93.
⁸ 刘雪阳.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探析[D].吉林大学,2022.
⁹ 许丽红.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中“明知”的认定[D].西南大学,2022.
¹⁰ 孙金发.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限缩适用[D].青岛大学,2022.
¹¹ 王茹仪.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入罪边界——以限缩适用《刑法》第287条之二为视角[J]. 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22,(14):100-103.
¹²王孟昕.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22.
¹³ 唐逸伦.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D].武汉大学,2022.
¹⁴杨佩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律问题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22.
¹⁵ 刘一帆.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D].吉林大学,2022.
¹⁶ 李永超,王丽.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明知与情节严重的认定[J]. 人民司法,2021,(35):24-26.
¹⁷ 张丁也.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21.
¹⁸ 魏维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D].贵州民族大学,2019.
¹⁹ 陈洪兵.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限缩解释适用[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6(01):109-117.

扫描二维码添加企业微信